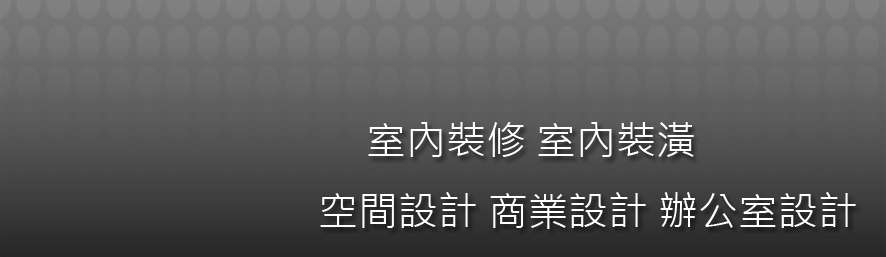文章来源:由「百度新聞」平台非商業用途取用"http://www.thepaper.cn/newsDetail_forward_5108691"
三明治關注原創:船長三明治編輯|童言2012疼痛等級:42012年3月,那是一個健身的下午。我剛做完上斜臥推,坐起身,按了按充血的上胸。按到左鎖骨近肩關節的一點時,一股陌生、尖銳的疼痛猛地擊中了我。起初,我以為連接鎖骨的肌肉酸痛或拉傷了,并沒有理會,但這疼痛仿佛在我身上生長——第一周,從左鎖骨的一點擴散到了整條左鎖骨。第二周到第三周,左鎖骨上的皮膚紅了,周圍的肌肉組織灼熱而水腫。大約從第四周起,頻繁的疼痛和發熱開始讓我難以入睡。我這才意識到,它不是什麼拉傷,而是更嚴重的問題。即便是那時,我依舊是樂觀的,以為只是哪里發炎了,上醫院打個針就能痊愈。第一次去市中醫院檢查時,我還抓著一本GMAT的詞匯書。那時我在備考GMAT,計劃著申請一所美國的大學讀金融。那次檢查只查了兩三管血和一張鎖骨的CT,并沒有查出什麼。醫生讓我注意休息,第二天開始做一療程針灸。4月初,針灸的療程還沒結束,我就受到爺爺奶奶的召喚,前往蘇州探親,順便進行更徹底的檢查——奶奶以前在衛生局工作,她從不放過任何小病小痛和那些聳人聽聞的養生小文章——她會把那些文章先轉發到家庭群,再一個一個單發,她是個很可愛的老人家。在蘇州的檢查結果似乎不大樂觀,在進行了MRI檢查后,我爸從北京飛過來,和幾位醫生聊了半個小時。“仔,問題不大,但保險起見,我們還是去上海好好查一查吧。”從骨科醫生的辦公室出來后,他是這么說的,語氣輕松平淡,要不是疼痛有增無減,我幾乎要相信自己快要痊愈了。2012年的整個夏天,我往返于深圳和上海。而每次一到上海,就直奔六院的骨科樓,隨后是連續數日的檢查和輸液,偶爾有個空閑的下午,我會下樓吃一頓小楊生煎,然后走過天橋去逛新華書店。在深圳,我則在備考GMAT和寫作向大學推介自己的文章。在7月的某一天,主治醫生楊主任終于給我下了診斷結果——骨髓炎,一種常見于老年人或骨折傷愈過程中的疾病。之后,我在上海住了半個月院,各種消炎藥輪番上陣,從我左手背上的留置針頭輸進血管。我躺在病床上,時不時用右手別扭地翻幾頁《雪國》,想象著大雪中的紐約,想象著自己痊愈后的樣子。5個月后,我在時代廣場停下腳步,發現紐約的雪是白中帶灰色的,被車轍和足跡污染了,和這個城市的主色調一致,也和我那時的心情一致。這個夏天的治療并沒有讓我痊愈,只是控制住了骨髓炎的發作,我帶著骨髓炎來到了美國,開始了留學生活。2013年疼痛等級:8如果不駕車,在新澤西州的南奧蘭治購物是很不方便的事。那里沒有外賣配送,也沒有幾家便利店,購買生活物資要靠離我的公寓近兩公里的大型超市。2013年2月,我雙手提著數只裝滿了水果、芝士、面包、飲料的大購物袋,沿著未清理好的雪路挪回了宿舍。當晚,我被鎖骨里的灼熱和斜方肌的筋攣疼醒,并開始發燒。我熬到了次日上午,實在忍不住了,去了離宿舍最近的圣巴納巴斯醫療中心。我從急診區域的通道走進了醫院,一進室內就聞到空氣清新劑的味道,人很少,安靜、清潔、冷清。一個步履輕盈、淺綠色制度的護士把我領到一張被布簾包圍起來的病床上。隨后是漫長的等待,和幾乎一個小時一次的檢查——檢查時,護士會用輪椅把我推到醫院深處的某個檢查室,結束后再推回這張病床。我說了我可以走路,但他們都堅持讓我坐輪椅。晚餐時分,我住進了二樓的病房。“你的疼痛等級是多少?”晚飯后,護士給我安裝了留置針頭,然后問道。“6?7?我不確定,至少是6。”我疼得有些面目猙獰,只想趕緊輸液。她愉快地點點頭,確認了我的姓名,才開始輸液。過了至少半小時,疼痛才不情不愿地減退了。我躺在病床上,想舉起手拿床頭柜上的手機,卻感覺右手抬不起來了。此刻我才發現,這次疼的不是左側鎖骨,而是右側鎖骨以及右肩關節。幾天后的影像檢查結果也確認了,我的右鎖骨也有了骨髓炎的癥狀。在此之前,我怎么也想不到骨髓炎居然會移動,這個事實擊倒了我。我躺在病床上,什麼也不想做了,一動不動地望著懸掛在一米外的小電視。電視在循環播放同一個節目,是幾個嘉賓坐在沙發上觀看無窮無盡的惡作劇視頻。視頻中出現了許許多多被擊中襠部,墜落,滑倒的人。“好疼啊,真的好疼啊。”那時我腦海里只有這一句話,翻來覆去,不知是在說視頻中的人,還是說我自己。幸運的是,我吃了一周國內帶去的消炎藥西樂葆,每天打兩瓶鎮痛藥劑,這次發作就結束了。三個月后,也就是在五月或六月的一個宜人的黃昏,透過出租車的暗色車窗,天空是粉藍色的,云朵像數只龐大而歪斜的水母,我再次因骨髓炎發作住院了。這次住院,我深刻地理解了protocol的意義。入院后的第一天,我希望醫生盡快給我幾針抗生素來鎮壓炎癥,醫生說因為protocols,他不能在確診前給我注射抗生素。又過了三四天,我又接受了一輪檢查,疼痛愈發劇烈,愈發不堪忍受,而我接受的治療卻只是每天兩針止痛劑。我聯系了國內的醫生,他也認為必須先鎮壓炎癥。我再次提出需要抗生素治療,美國的主治醫生說他們經過會診,認為我確實有骨髓炎,但他們相信,抗生素不是最合理的治療方案。“但我真的太疼了,疼痛等級10,10!你必須給我些抗生素。”我斜倚在病床上,虛弱、憤怒,近乎瘋狂。“我理解,但我必須遵守Protocols。我們會盡快確定治療方案的。針對你的疼痛,我想想辦法吧。”Protocol在美國的醫療系統里大概是“協議”或“規定”的意思,醫生口中的Protocols是抗生素使用的規定。而對我而言,它只是痛苦的延續。他想到的辦法是一天兩針杜冷丁,但杜冷丁已經處理不了當時的疼痛了。一次注射只能輕微地緩解兩到三個小時的疼痛,而一天有二十四個小時。我又熬過了一兩天,等待醫生們確定治療方案。如果明天再沒有方案,我就休學回國,我已經確認好從紐瓦克直飛上海的機票了。次日清晨,我的主治醫生用異常樂觀、開朗的口吻向我描述了手術的過程——先將左鎖骨取出來,像劈竹子一樣縱切開。“就像這樣!”,他用生動的手勢來配合說明,用手劈砍的動作是那么輕快有力。然后,把骨髓刮干凈,再填充一些材料,手術就完成了!他提供的治療方案就是手術,這是他唯一的方案。我愣了一兩分鐘,然后絮絮叨叨地問了他不少問題。他以輕松的語氣向我一一說明,大意是,術后我的骨骼的承力當然不比普通人,運動幾乎是不可能的,但日常生活問題不大。他微笑著點了下頭離開了,或許是希望我也更樂觀地看待術后的生活,又或許那是解決了難題后的喜悅。我聯系了國內的醫生和我的父母。我沒法告訴他們到底痛到什麼程度,但我明確表達了關于手術的意愿——如果手術確實能一勞永逸地解除病癥,那我可以做。如果它不一定,那我寧可繼續疼下去。國內的醫生們進行了兩次會診,建議不進行手術。他們郵寄了一箱口服消炎藥,我撐到了假期回國。接下來的12天,是我至今的人生中,經歷過的最狂暴的疼痛。我幾乎不停歇地在病床上翻滾扭動,壓低聲音呻吟,每過幾分鐘就按鈴問護士下一針藥還有多久或者換一袋冰袋。一針嗎啡也是吝嗇地給予我兩小時的睡眠時間,之后就被疼醒,繼續下一輪折磨。前兩天,醫生給我一天兩針嗎啡。之后,醫生發現我實在不行了,就給我一天四針嗎啡。然而,這已經極限用量了,如果再增加,嗎啡成癮的概率會急劇上升。如果要形容一下那是怎樣的痛,可以這么說,我的左肩關節、左右鎖骨都仿佛被注入了熔巖,一舉一動都會讓這熔巖就蕩漾濺射,化作萬千根鋼針反復穿刺著肌肉、骨骼和神經。我只有完全卸去力氣,癱在床上,疼痛才能稍稍緩解——緩解十分之一。疼痛讓我經常想象死亡。自從初次理解了死亡的存在,在小學四年級的一個夜晚,我對它的印象就固定了——一個無光、冰冷的星球,地表豎立著一排排不可思議的偌大墓碑,我以星球外的視角凝視著自己的墓碑,想象自己無法思考時的世界。這副印象圖對我而言是無比恐怖的,一旦去想象,血液凝滯,手腳也隨之冰冷,仿佛在想象時觸到了死亡的裙角,我會猛地大口喘息并迅速轉向別的思考。對那時的我而言,死亡卻是無限的酣暢沉睡,也是永遠消滅疼痛的良藥。我嚴肅地計算死亡的損益,計算我的未來是否值得我去承受這無窮盡的痛苦。直到我想到了我的母親,她很愛我,對我的疼痛幾乎感同身受。我的骨髓炎也給她帶來了巨大的痛苦,讓她一次次痛哭流涕。我的疼痛會傷害她。因此,我不怎么告訴她真實情況,只說我的身體越來越好,幾個月都沒有發作了。然而,母親的存在也是我最大的保險。如果我選擇離世,這一定會徹底摧毀她。因此我必須活下去,好好活下去,希望在未來,真的有越來越好的一天。這12天過后,疼痛一天天消退了。骨髓炎的來去,大多是莫名其妙的。2015-2016疼痛等級:6也許會有人不理解,為什麼我直接跳過了2014年。不必好奇,因為我的2013、2014和2015年上半年幾乎是三胞胎。飛到美國,學習,休息,骨髓炎發作,住院,骨髓炎轉移到骶髂關節,假期回國,住院,休息,飛回美國——不外乎這些事,沒有太多可以說的。2015年夏末,我終于回國了。回國后,骨髓炎發作時,可以在本市找醫院打抗生素和脫水劑,同時口服消炎藥,一般兩三周就能控制住炎癥。平時,我每天吃三次消炎藥,并盡力避免可能誘發炎癥的行為。我患的骨髓炎最終被診斷為自免疫性骨髓炎,屬于慢性病,沒有什麼有效的治療方法,只能減少它的發作,等待自愈。“這病沒什麼,總有一天會好的!楊主任看了那么多病人,他很有把握地告訴我,發作會越來越少的,還有不少患者到了五六十歲它莫名其妙就好了。”父親那土匪式的豪邁和幽默,常能把我從焦慮的泥潭拉出來。他會在我檢查了一天后,帶我去醫院附近吃一頓大餐,牛扒,潮汕火鍋,或是上海菜,次日再飛回北京。2015年秋,我回到深圳的家,在人生的分岔路口徘徊不前——我應該盡快開始工作,還是先把身體養好?經歷了三年的反復發作,我的身體完全透支了。即便是不發作的時候,也總有一邊鎖骨是微微水腫的——有趣的是,它們從來沒有同時水腫過——鎖骨同側的斜方肌會如鐵塊一般僵硬,不受控制地筋攣。同側的手臂一舉過肩,就會引起令人不快的脹痛,這讓套頭衫顯得格外面目可憎。骶髂關節的骨髓炎是難以通過藥物控制的,它只聽氣候的指揮,一旦氣溫低于20度,或是急降溫,我的左臀內就仿佛扎了根鐵釘,起床、坐下、行走都會帶來炙熱的疼痛。痛苦重塑了我——這句似乎空洞又煽情的話,對我而言就是生活。病痛是橫臥在我人生路上的巨樹,它堵住了許多條路,只留下兩三條杳無人跡的窄路。工作、鍛煉、戀愛、享樂......似乎都是不可能的。那時的我,急需找一個有意義的目標,讓痛苦本身也具有意義。我開始閱讀。從王小波到哈代、陀思妥耶夫斯基,從村上春樹到托爾斯泰、菲茨杰拉德,從納博科夫到卡夫卡,從伊恩·麥克尤恩到愛倫·坡,從米蘭·昆德拉到尼采,從毛姆、木心到兩部《文學回憶錄》中數不清的作者——從一本書連接到另一本書,從一個作家連接到另幾個作家。我面前展開了一個生生不息、無限相連的世界。我著魔一般地讀了一整年,讀完了82本書,幾乎忘記了疼痛和不便,且得了痔瘡。在痔瘡出血的那周,我買了本紫色封面的《海德格爾》。海德格爾的哲學攫住了我,因為它闡明了痛苦的意義。他認為,死亡始終在場,它陪伴每一個生命,不曾離開。非本真的人們沉淪于日常,沉湎于欲望,他們忽略了死亡的在場,以仿佛能永生的心態生活。而時刻不忘死的在場的人們,才能找回其本真性,找到他們最真實、最絕對的理想。“此在”,德語是dasein,意為具有本真性的人們,并非所有人都是此在。疼痛不斷地向我提示死亡的在場,它剝去我層層疊疊的欲望,讓最本真的內核暴露了出來——我想寫作。我想把自己那不值一提的思想化作文字,想把經歷過的、幻想過的、夢見的故事寫成小說。我必須馬上開始,在身體被骨髓炎消耗殆盡之前,全力以赴地寫作。《決定論與自由意志——對康德倫理學的簡單說明》、《先驗與超驗》、《從波伏娃開始》、《關于克爾凱郭爾——論自由》、《讀會飲篇》、《鳥的沉思》——最初的的文章大多是用淺白地文字去介紹哲學家的思想,并在寫作中梳理自己的理解。2016年底,我開始寫小說。寫完的第一部小說叫《邂逅一個故事》,講的是重病住院的主角,遇到了一位奇妙的少女。少女每次與他見面時,都展現出不同的靈魂——《樹上的男爵》、《包法利夫人》、《夜色溫柔》、《黃金時代》,以及《白夜》中女主角的靈魂。少女的自我在與這些靈魂的糾纏中,逐漸迷失了。主角想認識她自身的靈魂,卻見到一連串令他眼花繚亂、目眩神迷的表象。顯然,這部小說寫得很糟糕。過多的場景描寫,生澀的對白,不合理的人物設定,使它幾乎讀不下去。但是,它給我帶來了無法言說的洶涌快感,并讓我確信,寫作中的我才是最本真的人,才可被稱為此在。如果能繼續寫作下去,一切過去的、現在的、未來的痛苦都是值得的。2017-2019疼痛等級:2醫學是一門實驗科學——讀初三時有個朋友這么告訴我,他把一切科學都分為理論的或實驗的。當時,我心不在焉地回應著他,手肘支在護欄上,隔著天井眺望教學樓對側的幾個女生。2017年,我在一次次對自身的實驗中,回憶起這段往事——我懷念當年那靈活、柔韌、無痛的身體,還發現朋友當初的話是對的。2017年初,在六院的楊主任與姚主任的建議下,我開始使用恩利——一種對骨髓炎效果不錯的生物制劑。在它的作用下,那附骨之疽的疼痛潛伏下來。人類也許有遺忘疼痛的本能,在我過了幾周無痛的生活后,那備受煎熬的過去就仿佛從未存在過。這種本能會讓人重復過去的錯誤,但也給予人從失敗中站起來的勇氣。這幾年間我見過十多位醫生,聽過數十次會診的結論,卻依然不知該如何避免炎癥的發作。我希望知道如同1+1=2一般絕對清晰的法則,但醫生們的建議卻總是籠統的——好好休息,規律生活,注意保暖,適當鍛煉。這當然不是醫生的問題,只是生活中的變量太多,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很大,疾病的表達也因人而異——畢竟,醫學是一門實驗科學。為了知道如何在生活中避免炎癥,我開始了對自己的實驗。首先,每當炎癥發作,我都會回溯發作前的三到五天的生活,記錄其中的變化——氣溫的變化,濕度的變化,飲食的變化,壓力的變化......躺在病床上輸液時,我有充足的時間去思考、分析、判明這次發作的原因,一條條記錄在備忘錄里,并在未來盡量避免。當然,規避一切可能誘發炎癥的行為,是最穩妥的選擇。以炎癥為理由,一直在家休養似乎也無可厚非。但我做不到,我不想永遠被這些界限綁縛。既然沒人告訴我絕對的界限在何處,那今天記錄下的界限就不會是我的上限——即便是今天的上限,也不一定是明天的。2017年中旬,我走進了闊別多年的健身房。學習任何訓練動作時,我都會進行多輪的測試:先觀察在完成動作時肩關節、鎖骨、臀部是否有不適感;如果沒有,增加一定負重再做一組動作;若依然沒問題,就看訓練后的三天內炎癥是否會發作;如果沒有發作,我就把這個動作暫定為安全的動作,緩慢地增加負重,并持續關注身體的反應。健身對普通人來說是一項不斷挑戰自我的運動,但對我而言,它更像是化學實驗。不合適的動作,不合理的劑量,不合規的操作,或是環境的影響,都可能調制成骨髓炎的爆炸。每一次肌肉酸痛、韌帶拉傷、關節作響都讓我膽戰心驚,擔心自己會在凌晨冷汗涔涔地被疼醒,一夜無眠之后趕去醫院輸液。讓我堅持下來的,是一個樸素的假說——隨著身體素質的提高,骨髓炎的發作會越來越少。這是實驗的最后一環。2017年,它發作了8次。其中6次是由于氣候的變化——一日之內降溫9度,綿延兩周的暴雨,冬季睡眠時室溫過低等。另外2次則是健身的新動作誘發的。炎癥發作的話,通常口服藥一兩周就好了,其中3次較嚴重,必須輸液并配合口服藥,三周左右才恢復。這一年的發作看似不少,但頻率和程度,都已遠遠小于往年的水平。2018年,共發作了4次,沒有必須輸液的嚴重發作。2019年,至今共發作了3次,沒有必須輸液的嚴重發作。我一邊探索骨髓炎設下的邊界,一邊不斷突破著這一道道邊界。就像你在幽暗的密林中開路,劈砍樹枝時的反作用力震裂虎口,銳利的葉尖劃破皮膚,毒蟲叮咬出腫包或紅疹,但偶爾會發現一小片林中空地,陽光灑落在青草、樹葉、巖石上,也終于落在你的身上,溫暖你,治愈你,給予你力量走向下一片光明。骨髓炎或許會伴我一生,但這個故事到這里就結束了。我停下筆,望向窗外,陽光灑落在樹葉上,那是多么絢爛、輝煌、無盡的綠色。左肩關節傳來輕微的疼痛,多半是昨夜的降溫導致的。這一刻,我發現自己早已不恨骨髓炎了。作者后記:在寫這篇文章前,如果不算上學生時代的作文,我從沒有寫過非虛構的故事。與哲學和小說相比,真實發生的、需要回憶和考證的故事,似乎不夠自由。第一次發現非虛構寫作的力量,是讀了母親寫的往事。她多年來有一個習慣,就是用文字來把某些往事封印起來——按她的話說,我把它們完完整整地寫下來后,就不用再記在腦子里,也就不會翻來覆去地回憶它了。于是,我報了三明治的課,希望能寫下第一篇非虛構故事。寫作的過程并不容易,第一稿和第二稿我是按關鍵詞寫的,不僅寫成了流水賬,文段的時間軸也很混亂。在童言的多次建議下,我按時間順序重寫了全文,調整了詳略,才算逐漸成型。人有規避痛苦的本能。即便是在寫作時,我也試圖用客觀描述來替代疼痛的具體感受。而寫作導師告訴我,個人感受的描寫,才能讓讀者與你的故事產生共鳴。我回憶了許久,才挖出當時最疼痛的感受,寫進文章。在這個時代,寫作并不被市場鼓勵,但寫作對自身的回報是無限的。希望我永遠不會忘記這一點。閱讀原文
關鍵字標籤:美國波士頓留學代辦推薦-IDP Taiwan
|